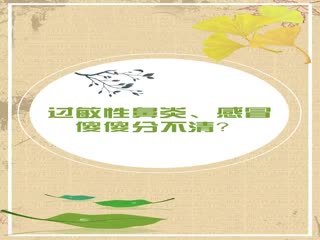基本药物制度实施步入“深水区”<br>国家发改委正在进行价格调研
- 作者:蔚佳
- 来源:中国医药报
- 2014-09-06 09:06
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出一年之际,有权威渠道消息显示,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对基本药物价格的调整进行调研,以努力体现价格“有升有降”的动态调整。
随着“天价芦笋片”等事件的曝光,此项新医改中的重要制度建设再次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在新医改中,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被寄予降低药价的厚望,经过一年的实践,其中一些新问题已开始显现,亟待进行更深入的调整和突破。
公权力越位之忧
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中,对基本药物和补充药物统一招标采购的规定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而在具体实施中,“地方保护”等以往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中的旧疾沉疴在基本药物招标采购中再次显现,引起业界重视。
招标工作启动后,四川某著名药企的副总就一直拖着行李箱四处奔波。他表示:“每个省的招标规矩和需要的文件都不一样,我们招标办原来有4个人,现在增加到10个人,还是忙不过来。”
早在2009年冬天,一些先行启动招标工作的省份和地区就逐渐发现,基本药物招标过程中出现的企业低价竞标和缺乏操作规范等问题,似乎成为了一个“典型症状”。
2009年11月6日,福建省出台的《国家基本药物集中采购实施方案》规定:“本省医药生产企业生产的产品(含药品、医用耗材及检验试剂),经过企业及药品资质审查合格的,申报的价格不高于同类药品入围价的,经过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后可直接入围挂网。”
此外,规定中还明确表示,“每个确标单位按药品通用名、质量层次、剂型各确定1家生产企业入围,但福建省的企业同等优先”。
“这就意味着,价格水平相当的情况下,不论质量如何,只要是福建当地的企业,就可以直接晋级。”四川某著名药企负责人表示,为了保住福建市场,他们不得不在当地收购了一家小型药厂。
“其实根本没用,但医院用药市场占到80%,所以只能想办法先拿到一个‘福建户口’参加招标。”他说。
5月10日下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山东省近百家与潍坊市各级医院有业务往来的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医药商业公司,被医院单方面取消了药品配送资格,所有医院使用的药品被当地卫生局要求只允许由山东潍坊海王一家医药公司配送。
公开数据显示,潍坊市50家医药商业企业中有35家取得省级采购的统一配送资格,每年完成营业收入40亿元以上,上缴利税5000万元。不仅如此,潍坊一地的医药商业份额就占到了山东全省的三分之一。在全国医药强省山东,潍坊也是“兵家必争之地”。
“会上,一位政府机关的领导就是这么要求的,医院必须和潍坊海王一家签合同。”潍坊下辖某市卫生局局长随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
而一个月后,重庆市渝北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重庆天圣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状告重庆市卫生局一案,将产业与地方政府之间在基本药物上的矛盾推向了顶峰。
低价怪圈显现
“很多地方都不看厂家不看品种,要想参加招标,先砍价15%~20%,砍完了还要再往下谈,毫无科学性可言!”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在了解了多省区的招标情况之后叹道。
杭州中美华东制药有限公司的“赛斯平”主要用于抗移植排斥反应,2009年该药品以增补品种身份进入了浙江省基本药物目录,但该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和很多省份招标的态度一样,浙江省内也规定,要进入招标就必须先降价15%。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该负责人表示,虽然目前由于单品种招标,对销量的影响还不明显,但他担心的是,一旦明年使用范围增大,影响必然迅速显现。
“不同品种不同成本的药品,必须统一降价15%,这个科学依据究竟是什么?我真的很不理解。”他强调。
事实上,在大部分省份的招标书中都明确规定,总分100分的情况下,药品价格占60分、企业规模占15分、销售服务占15分、药品质量仅占10分。
随着时间推移,来自终端使用环节对基本药物的不积极现象开始逐渐向下显现影响。
“对基本药物的市场开始过于乐观,现在难免悲观。”于明德表示,“有些企业现在已经开始减少供应,有些甚至已经因为价格超出了成本承受极限,悄悄暂停了在某些地区的招标,等待下一步的政策出台。”
不久前,有400年历史的广州陈李济药厂承认,由于在当地招标中最高限价19元根本不可能保证品质,其代表产品乌鸡白凤丸已暂停在基本药物目录内的生产供应。
此前,同仁堂也迫于竞价压力,药品品质无法保证,暂停了某些省份的招标。
而包括北京双鹤药业在内的一些企业,由于政策不明朗,实际上一直没有生产某些品种。
“双鹤药业在基本药物目录里的品种有30多个,但是现在生产供应的也只有3个。”有接近双鹤药业方面的人士表示,“各地招标价格太乱了,根本没法做。”
在北京一项关于200家基本药物生产企业的调查中,85%的受访企业基本药物品种的毛利率在20%以下,65%的企业只生产出基本药物批文数量50%的品种,50.4%的受访企业表示当中标价格低于企业的基本利润时减少基本药物的参与,更有18.2%的企业表示不再参与。
财政重负难担
对于地方政府和当地医院对基本药物使用缺乏热情,在制度设计之初就有担心,因此,医改文件中特别强调对于基本药物的使用要制定相关文件加以约束和激励。
今年年初,全国卫生大会上,卫生部部长陈竺在谈及去年的基本药物制度工作时就表示:“有些省份的基本药物工作迟迟未见进展,特别是在一些经济发达省份,财政不能跟上,是说不过去的。”
但问题在于,由于基本药物采取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筹资形式,出钱的地方政府对此政策难免缺乏热情,而即便是有心推动,对于医院被拿掉的15%药品加成的巨大缺口,在公立医院改革还未真正开始,没有其他收入来源的时候,政府又该从有限的财政中拿出哪一部分补上?
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教授曾对基层医疗机构使用基本药物的情况做了实地调研。他认为,在药品收入占到整体收入70%,甚至80%的基层医院,基本药物取消药品加成后,恐怕将难以为继。
石家庄制药集团有92个品规进入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其负责基本药物工作的高级总监张永泰告诉媒体,他们现在最担心的问题就是,补偿机制不到位的话,乡镇卫生院恐怕会“想别的办法”。
张永泰认为,要求药厂返点或者要求换用别的药物,如果这些潜在的问题变成现实,就意味着同一药品的零售价可能在一座城市都会各不相同,而这种价格紊乱对工业企业造成的伤害和管理困难也许会引发更大的质量问题。
张永泰表示,不少地方正在进行二次议价,某些地方甚至需要一个县一个县地去谈价格,对配送渠道的要求也不一样。“基本药物招标国家统一规范现在还没最后出来,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据海宁市卫生局的同志介绍,9000万元经费缺口,海宁市财政能够提供的补偿只有500万元,省财政明显也没有这个财力。”朱恒鹏指出,事实上,以浙江省为例,实施基本药物“零差价”制度形成的医疗机构经费缺口,全部由省县两级财政全额补偿,浙江省两级财政年度支出也需要增加100亿元以上。
“尽管是全国经济最发达省份,浙江地方财政也负担不起这笔支出。尤其是实施基本药物制度后,这笔支出就成为年年必须开支的常规性支出。”朱恒鹏表示,“我们真切地感觉到,基层医疗机构很清楚财政无力足额补偿这一事实,所以普遍对‘零差价’制度持消极观望态度,明显缺乏实施动力。”
公开资料显示,2009年,全国各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负债总额达到5万亿元以上,各地区投融资平台负债率超过80%,实际情况可能更糟——在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水平已经很高的情况下,地方财政对基本药物制度实施后取消药品加成的补偿,即便有心,也很难有此实力。
期待政策补位
“一些基本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比如补偿、配套的制度建设等等。”中国新医改课题组组长、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顾昕教授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尽管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并不支持取消药品加成后对公立医院的财政补偿,但顾昕认为,相比“授之以鱼”的直接补偿,“授之以渔”的政策放开是紧要且必需的。
他认为,在基本药物政府埋单的大前提下,想要保证“优质低价”的药品能持续供应,保证基本药物制度的初衷达成,关键是要让这些药品有市场。“但现在,从我们调研的结果来看,很少有哪个省份的卫生部门和医院有足够的热情使用基本药物,这个问题,谁来埋单?”顾昕说。
但由于相关制度的滞后,截至目前,各地对于基本药物的使用热情依旧没有明显提高。
据悉,目前《基本药物采购规范》已在进行最后一轮征求意见,近期将正式对外公布施行,而早在公布目录中的招标配送等文件也将在年底前向外发布。
“虽然不是最关键的文件,但这些至少可以先规范招标采购中的行为。”国内最大的民营医药流通企业湖北九州通副总经理牛正乾认为,“加强医院使用基本药物的动力,关键在于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医改有实效了,药才可能真的发挥作用。”
(责任编辑:)
分享至
右键点击另存二维码!
-
相关阅读
-
为你推荐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10120170033
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京)字082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23089号 京ICP备17013160号-1
《中国医药报》社有限公司 中国食品药品网版权所有


dac00ec8-88f7-45fd-9248-d0bb4b6a357e_260x150c.jpg)